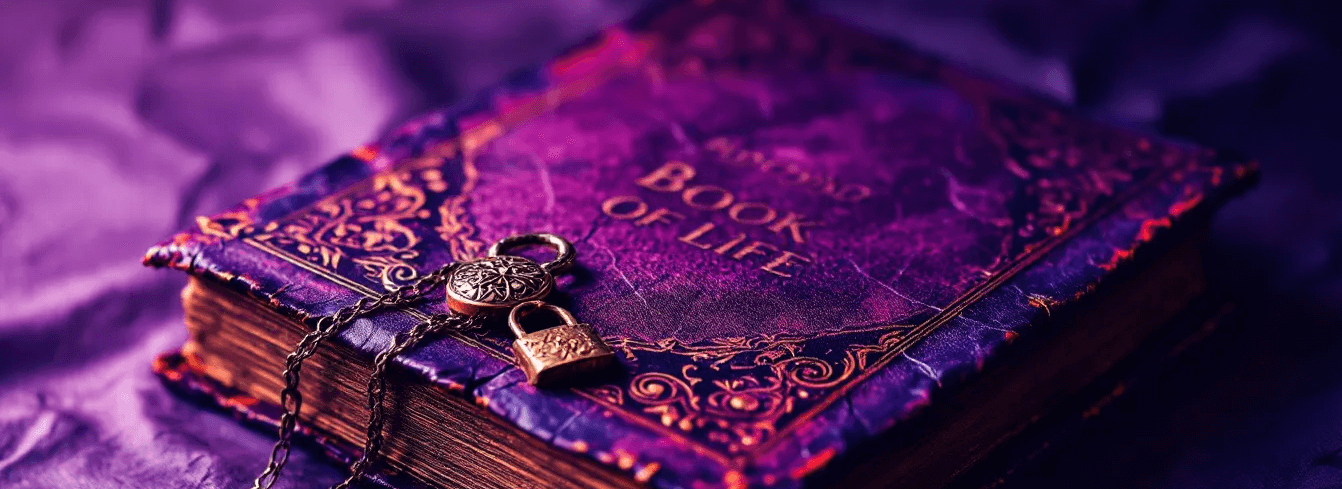
永厚 黄
视金钱如粪土,坚守艺术与人格的崇高追求。
Register of the Holy Name
- 90 years old
- Born on 1928-01-01 in China
- Passed on 2018-08-07 in China
黄永厚是中国著名的画家,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是著名画家黄永玉的二弟。黄永厚擅长中国画,其作品风格独特,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表现力。他的代表作品包括《九方皋》、《渐江》、《桃源》、《聊斋人物》、《阮籍》等,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艺,也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诠释。
黄永厚不仅在艺术创作上有着卓越的成就,他的人格魅力也为人称道。他经常鼓励画家多读书,关心社会问题,认为艺术家的责任不仅仅是创作美的作品,更应关注社会现实。他视金钱如粪土,曾有不少人愿意出重金向他求画,但他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艺术原则和道德底线,拒之门外。这种高洁的品格和坚定的艺术追求,使他在艺术界和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赞誉。
2018年8月7日,黄永厚在安徽合肥逝世,享年91岁。他的一生不仅为中国艺术界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也为后人树立了艺术与人格并重的典范。
Path of Grace
- 1928January 1th
出生
黄永厚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
湖南省凤凰县
- 2018August 7th
逝世
黄永厚在安徽合肥逝世,享年91岁。
安徽合肥
Hall of Grace
Register of Return
"The only real treasure is in your head. Memories are better than diamonds."
- BOFM
陈远——辞不达意的怀念
《书屋》杂志创刊的时候,我读中学。刚创刊的《书屋》,真是厉害,竟然发行到了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县城。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我对所有的杂质报刊都充满了兴趣,每次到了报刊亭,不由分说的就把那些有点文艺气息的杂志买走。正是在书屋杂志上。我第一次见到黄永厚先生的画,具体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当时给我的冲击至今还印象非常强烈。
就是这位黄先生画画和我之前看到的国画不太一样。
人家画画,都有个模本。画牡丹就是牡丹,画梅花就是梅花,第一次画和第二次画,看上去都一模一样,当时在我的认识中,那样的画家才叫厉害。这位黄先生,却不是这样,他既不画花卉,也不画山水,说他画人物吧,好像也不是那么像。
但是很奇怪,这位黄永厚先生的画,却让人很难忘。
从那以后,我对于黄永厚先生就开始留心起来,每次看到他的作品,都会细细的琢磨半天,因为,他的每一幅画,都有一段长长的跋,读起来有些诙谐,似乎又别有深意。不好好琢磨一番,就很难得其要领。
再后来《书屋》的封二,就换成了黄永玉先生画。
我读大四那年,书屋的主编聂乐和到石家庄组稿。我跟大学老师谢志浩先生一起到宾馆去和聂先生聊天,其间我还问了一句,书屋最早封二不是黄永厚画吗?怎么后来忽然换成了黄永玉?聂先生听我问这个问题略微一愣,一语带过:黄永玉的名气大一些嘛。
稍后又补了一句,这哥俩很有意思。
当时我身处石家庄,消息闭塞,对这句话,并没有放在心上。
大学毕业后,确定了以历史为自己一生的志业,读史阅世,忧世忧生,早年对于永厚先生的关注,也就暂时放到了一边。没想到的是,从石家庄辗转北京的我,竟然能够和永厚先生相遇,并且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追随。
2005年,那时我正在新京报做记者,席勒去世20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召开,北京文化界名人一时云集,永厚先生自然也在受邀之列,承摄影家李晓斌兄介绍,我得以认识永厚先生。
我的“长辈缘”一向很好,纪念会结束之后,我和永厚先生俨然已经像认识了多年的忘年交。
自那以后,我便常常叨扰,或电话,或上门。浑然忘记了第一次登门时,永厚先生门上贴的“闲谈不过半小时”的字条(事隔多年,字条的具体内容已记不清,大意如此)。
但永厚先生对我的频频打扰似乎并不介意,反倒还有几分喜欢。这也让我再打扰他时,少了几分忐忑。
随着越来越熟悉,发现永厚先生,不但不是不喜欢闲谈,而是非常喜欢闲谈,只要是跟他谈人文领域的话题,基本上开了头就没完。老爷子虽然足不出户,但是对人文领域的动态了如指掌,我自谓读书庞杂,但经常是有些人文领域的新消息,还是从老爷子那里听说。有时候,他读书到酣畅处,会给我打个电话,用很兴奋的语气告诉我谁谁又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观点,每到这个时候,他总是会说:你不要说话,我给你读一段儿啊……如果是去老爷子家里拜访,案头上永远是一本正在读的书和正在写的密密麻麻的眉批。可是如果要是聊家长里短,聊不上三分钟,老爷子就兴味索然。
在他的客厅里,有一幅黄永玉先生大幅画作。画作上,永玉先生的题跋是: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吾家老二有此风骨。这真是永厚先生的写照。
我曾经问他,你是一个画家,却为什么却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在读书上?
老爷子说:我是一个画家,可也是一个读书人。我自知自己底子薄,过去读书少,现在要拼命的补回来。大多数的画家用了很多的时间,耗费在笔墨功夫上,不能说人家不好,但是我的画,是要表达我的思想的。我从来不为自己的笔墨功夫不如人感到羞愧,但是要做到每一幅作品都能表达出一个自己的想法。
这实际上是老爷子的谦虚之词,论笔墨,他并不输于同侪,刘海粟,赖少奇,亚明,朱屺瞻等前辈画家,都曾经对他有极高的评价。但是他笔下的作品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却是同时代的画家们所没有的。
韩羽先生曾经这样评价他:就画跋看,白石老人着眼所在,仍是士大夫眼中的博学。黄永厚却从郑家婢的博学里看到了蒙昧,黄从《世说新语》里迈出了一步。白石老人,说句冒犯的话:“仍在原地打转转。”
中国书画,有着非常巨大的传统,在里面打转转容易,真正迈出一步,难之又难。
只是这样的作品,不免曲高和寡,在时人眼里,究竟还是花花绿绿的花鸟山水更好看,再加上老爷子有些孤傲的性格,使得他生前少为大众所知。
但在圈子内,老爷子的水平有口皆碑。
在我追随了老爷子几年之后,有一次在朋友聚会的场合,坐我对面的一位先生,书法家刘炳森的弟子,他忽然问我:听你谈吐与见识,似乎应该有师承?我答之跟随永厚先生。那位先生离座起身,走到我身旁与我握手:二先生是了不起的人物。
我回去后告诉永厚先生,他自然也是高兴的,但也仅仅是高兴而已,并不以此自矜。
我和永厚先生,原无师徒名分。2008年我搬到通州居住,当时买房未曾刻意,不想竟和永厚先生成了邻居——从我们小区走到永厚先生居住的小区,仅需一刻钟的时间。永厚先生知道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画了一幅大画儿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取。那时候,永厚先生的画价已然不菲,我于是懦懦的推辞:这是不是太贵重了?老爷子哈哈大笑:“也不是每天都能卖出去。有时候出门,楼下的邻居用车送我,我也会画张画,充当车资。”我于是不再推辞。
住的近了,来往自然也就更加频繁。在后来我们聊天的时候,关于书画的内容逐渐多了起来。
从上古铭文到汉魏的摩崖碑刻,再到晚清民国的文人笔墨,老爷子为我打开了一扇与我之前的认识迥然不同的艺术大门。我对于书画的兴趣,也再一次被老爷子激发。
喝了老爷子多少茶,抽了老爷子多少烟,已经无法统计,但是我对中国书画的认识却越来越系统而清晰。
有时也大着胆子写几个字,拿去给老爷子看。老爷子看了之后总是一副赞许的样子。遇到他兴致高的时候,他会拿起笔来,再写一遍我写的内容给我看。每次看完之后,我内心的自得就转为羞愧。
对于我的内心活动,老爷子明察秋毫:
你别着急,慢慢写,写字画画是没有捷径的。但胆子不妨放大一些。你总是看我写的好,不过是因为老头子活的年纪久,写的比时间长,脸皮也要比你厚,不太在乎别人怎么说。可是你一写字呢,总是担心人家说你,陈远这个字写的不好,又要想着,这个字颜真卿是怎么写的?柳公权是怎么写的?你这哪里是写字嘛?分明是自我折磨,写字应该是件快乐的事情啊!
大道至简,老爷子的话,仿佛捅破了一层窗户纸,让我对于书法有了自己的认识。
就这样,虽有师徒之实,但无师徒之名的状态持续了两三年。有一次我扭扭捏捏的和老爷子提出拜师的想法。老爷子没有搭腔,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简繁的《沧海》让我拿回家去看,一边自己嘟囔:可不要拜师,可不要拜师,你看看刘海粟,被他的好学生害惨了。
《沧海》是刘海粟的博士生简繁,给刘写的一本传记,书中写到了很多刘海粟先生不为人知的隐秘,极尽夸张,且虚虚实实。只是我有点诧异,我拜师和简繁的这本书有什么关系呢?
陆陆续续读完了那本书,我有些明白,黄老经历过非常年代,尽管他对这个世界的热情没有减少,但由于对人性有深刻的体察,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于当下的世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警惕和戒备。因为对这个世界太过热情,所以要在内心建立一个壁垒,以防自己受伤。有一次,我正在外地,黄老打电话给我:今天南方周末上发了一篇章诒he的文章:陈姑娘,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你看了没?我说没有。老爷子说你一定要找来看看。章诒he对于人情的体察,真是了不得。我找来南方周末,读了那篇文章,果然如此。那篇文章,在章先生的文章中,从话题上说算不上特别引人关注的。若不是黄老提醒,我也不会特别关注。这是两位对人心都有深刻体察的前辈的惺惺相惜。
大哥黄永玉曾经写过一幅聂绀弩的对联送给他:中年多隐痛,垂老淡虚名。隐约透露出永厚先生中年曾经遭遇坎坷。但我追随先生十几年,从未听他抱怨过,反倒常常说:上天已经待我不薄,大家都不容易。
有些事情反倒是后来听师兄黄河跟我说的。永厚先生中年时,常喜欢招朋引伴,自然有时就忽略了家庭,除了安风大姐和师兄黄河之外,他还有一个女儿,因为车祸而去世。女儿去世时,永厚先生正在与朋友们聚会,他接到电话,心中的悲伤可想而知,但仍然回到聚会现场,和朋友们一一告别,然后一个人走出大门,嚎啕大哭。
他内心有炽热的情感,又遭逢丧女之痛,一时无法排解,精神状况几近崩溃的边缘。故土的一草一木,都会引发他的伤感。师兄黄河看到这种情况,主动的承担起家中的事务,永厚先生则告别故土,只身来到北京。
80年代,师兄黄河大学毕业,从不喜欢办画展的永厚先生,决定办一次父子画展。那个时代虽然已经有了开放的风气,但是要办画展还是需要层层审批,一个只知道读书的书生,哪里应付得了这么多的环节?一变再变,最初计划在上海美术馆开展的画展,最终只能在冷清的虹口公园举办,也没有任何的宣传报道。
可是在画展的最后一天,几位上海画界的重量级人物:颜文樑、朱屺瞻、关良、钱君匋等人,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消息,纷沓而至。对永厚先生的画作,赞赏有加。事隔多年之后,永厚夫子拿着当年父子画展的照片,一面唏嘘,一面感激不已:这张照片,不知道当时谁给照的,这些人我那时一个都不认识。
彼时,永厚先生还在合肥工大任教。他讲的课虽然备受学生们的欢迎,却迟迟没有评上教授。后来方知道了这个情况,说:黄永厚这样的人不评教授,还有谁可以评教授?这样,永厚先生才成为一名教授。虽然他从来不以教授自夸,但是他的教授职称是方给评的这件事,还是让他颇为自得。
纵然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纵然对人性的幽暗有诸多体察,纵然在内心深处建筑隐秘的壁垒,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热情和自身的天真,却没有减少。
2001年,《现代化陷井》一书的作者去美之前,曾有过北京之行,当时何清涟的情况,大多数人唯恐避之不及。永厚先生听闻,自告奋勇邀集了一帮朋友请何清涟吃饭。“我那时刚好卖了几张画儿,手头有点钱,我带了8000块钱,结账时竟然不够,好尴尬,幸亏北京饭店的经理认识我,帮我解了围。”
大概是2005年,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王学泰你肯定认识,我读了他的一篇回忆文章,这个人太了不起,上高中的时候,就能够认识到亩产万斤不可能。我想认识他,我觉得他就是国士无双,我要给他画一张画。
那时还没有搬到通州的我,恰巧就住在王学泰先生家的附近,并且相处甚洽。我去给王学泰先生送画时,王先生说:黄老是前辈,他这样做,我怎么当得起?太惭愧了,你帮我问问黄老,他什么时间方便?我和我爱人登门拜访。王先生还跟我说了一件逸事,其实在此之前,王先生和黄老曾经在三联举办的一次读书会上遇到过,当时两个人就坐对面,王先生说:我认识黄老,可是黄老并不认识我,又担心别人说我高攀,所以就没有上前打招呼。我把这段逸事告诉黄老,黄老当即打电话去问拉他去参加读书会的朋友:你当时为什么不介绍我认识王学泰?那位朋友赶忙解释:我以为你们认识。
黄老从不以前辈自居,对于比他年轻的晚辈,总是不遗余力的鼓励和提携,这两件事情,在他的一生中,在他的生命中,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且不胜枚举。黄老去世之后,我在微博上看到许多年轻人,发自内心的怀念,无一例外的都提到了黄老对他们的帮助,让我比较吃惊的是,这些人当中竟然还有摇滚歌手左小祖咒和张楚。黄老一生帮助过多少人?他从来不曾说起过。
2008年,我在新京报受厄。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不曾到黄老家中拜访,他打电话问我为何如此长的时间没有露面?是否有什么困难?我支支吾吾。他于是直接的说:如果你在家又有时间的话,就到老头子这里来聊聊天。
我去了,老爷子单刀直入地说:我想你大概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又不愿老头子担心。可是说说无妨,万一我能帮得上呢。
我于是不再隐瞒,把自己当时的遭遇和盘托出。老爷子听完,面露难色,许久没有说话。后来,他说:你先回家,容我想想。我从黄老家下楼,心绪烦乱,就在他家楼下,一边踱步,一边不停的抽烟。
又过了两天,黄老又给我打电话:我给张思zhi画了一幅画,你能不能帮我给他送去?还有别人送我的上好的云腿,也一定麻烦你送过去。我当时未曾多想,应承下来。
见到张老,把黄老的画作和云腿交付,我就想离开。张老叫住了我:你的事儿,永厚跟我说了。我来帮你解决。
在张老的援手之下,我的处境得以缓解。
事后我去黄老家中汇报此事,他说,你走之后没有回家,在楼下一根烟接着一根烟的样子我都看到了,想着你还要赡养父母和抚养孩子,真是让人心疼。我那时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只好狠心把你赶走。
我再次提及拜师之事,黄老竟没有推辞。我问他要不要搞一个仪式,他笑了起来:想不到你年纪轻轻,脑子里还有这么封建的想法,搞什么仪式呢?我认你这个学生,你就是我的学生了。
不久之后就是端午,我带了自家包的粽子去黄老家里,他十分高兴:学生来看老师了。立即让家里的保姆把粽子热了来吃。
2014年,因为孩子上学,我把家从通州搬到海淀。搬家时各种忙乱,大概有一个月多月的时间,未曾给老人家打个电话问安。很罕见的,我也没有接到老人家打给我的催促电话。等我安定下来,打电话过去,电话却一直没有人接。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周。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黄老家的保姆,从上海打来的,告诉我黄老正在上海华东住院。保姆告诉我:黄老一开始担心告诉我,会给我增加负担,后来又担心我打电话找不到他着急,加上又十分想念我,所以让她告诉我情况。并且说黄老想和我通个电话,聊聊天。
我拿着电话,一时哽咽,不知说什么是好,只记得老爷子在电话那边一直说:我很好,你不要担心,也不要来看我,等出完院我就回北京了。
放下电话,我订了去上海的机票,赶往华东医院。老爷子看到我,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又责怪我:都告诉你了,不让你来。黄河和女儿这不都在吗?你赶紧回去安心工作。等我出院,咱们在一起写字画画。
不想在医院一住就是半年。老爷子生性好强,手术之后,假如衣冠不整,绝对不肯见人,哪怕面对的是自己的儿女也是如此。只是他明显见老了。
出院之后,老人家虚弱了很多,也消瘦了很多,加上有术后并发症,身边再不能离人。师兄黄河和大姐风安,为了便于照顾,把老爷子接回了合肥。
可是他的朋友们都在北京,合肥能够和他聊天的人很少,老爷子很是寂寞。每次我去合肥看他,他总会问到那些在北京的朋友:邵燕祥怎么样?林东海怎么样?宋红怎么样?王得后怎么样?……全然不顾我和这些前辈有些并无交往。但我又特别能理解老人家的心情。
2018年,4月份左右,有一天我接到老爷子的电话,他问我:我回合肥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来看看我?
我很诧异,因为自从他回合肥之后,我每年都会过去看望老人家。但当时也未多想,只是跟他说:等过些天,凉快一些,我过去看您。通完电话没几天,收到了老爷子从合肥寄来的作品,是我的画像,是我第一次和老爷子见面时的样子。老爷子说,他打算要写一篇文章,从他的老师张仃写起,然后一直写到我。这样就算是把关系交代清楚了。
事后想起来,他之所以不记得我去合肥看他,其实是记忆力已经开始衰退了。很多时候,打电话说不了多久,就会觉得疲惫。
进入五月,有一次打电话,是大姐风安接的,大姐告诉我,老爷子的身体状况不太乐观,偶尔会昏迷,并且不认得身边的人。
“他清醒的时候还是经常念叨你。”大姐说,“不过你不用急着过来了,有什么事儿我们再通知你。”
放下电话,我匆匆忙忙定了去合肥的车票。到了家里,看到老爷子的状况确实很不好,下床已经有些困难。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他睁开眼睛看到我,脸上露出笑容,要挣扎着坐起来。师兄黄河、大姐和我都笑了:老爷子还认识我。
过了一会儿,他又要挣扎着坐起来,执意让我们扶他到椅子上,让我给他铺纸。他要写字给我看。
只是他太虚弱了,笔总是拿不稳,这和我前几次到合肥看他的情况很不一样。前几次,他的身体虽然虚弱,但是一拿起笔,就神采奕奕,仿佛从来没有动过手术。但是这一次,他写了几次,都不是很成功。
他坐在椅子上,着急,叹气:他妈的,怎么就拿不稳笔了!
他写累了,让我扶他上床休息。
很想能够在合肥多陪他些日子,只是当时诸事缠身,最后只能一如往常匆匆返京。
8月7号,晚上10点多,接到师兄黄河的短信,永厚夫子去世了。泪水模糊了双眼,一直到现在,依然想不起和师兄黄河通电话时说了些什么。
我和颜家文先生,赶到合肥,去和永厚夫子见最后一面。他安静的躺在棺木里,我却看到了他一生挣扎却始终不屈的灵魂。
永厚夫子走后,我时常想起老人家,想记录下在他身边的点点滴滴,只是每次提起笔,却总是不能抑制住自己的情感,直到老人家去世一周年的今天,才有了这样一篇辞不达意的怀念。
我想,老人家在天堂应该一切安好,只是我再想和他通个电话时,再也无法拨出。
2019年8月8日
(此文由陈远先生授权昨日银行不作任何修改转载发布。在黄永厚先生一周年祭之日,陈远先生作为弟子写作此文,是一份深情而克制的生命见证,这不只是写给黄永厚先生,为了纪念,为了交待,也是他本人的成长史、精神地图,昨日银行在此郑重将他的文章与黄永厚先生的部分画作共同留存,愿他们的名,愿他们的记忆可以得以永恒的保存。)
Pray
"When you pray, be honest. God knows the truth anyway."
Leave the first p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