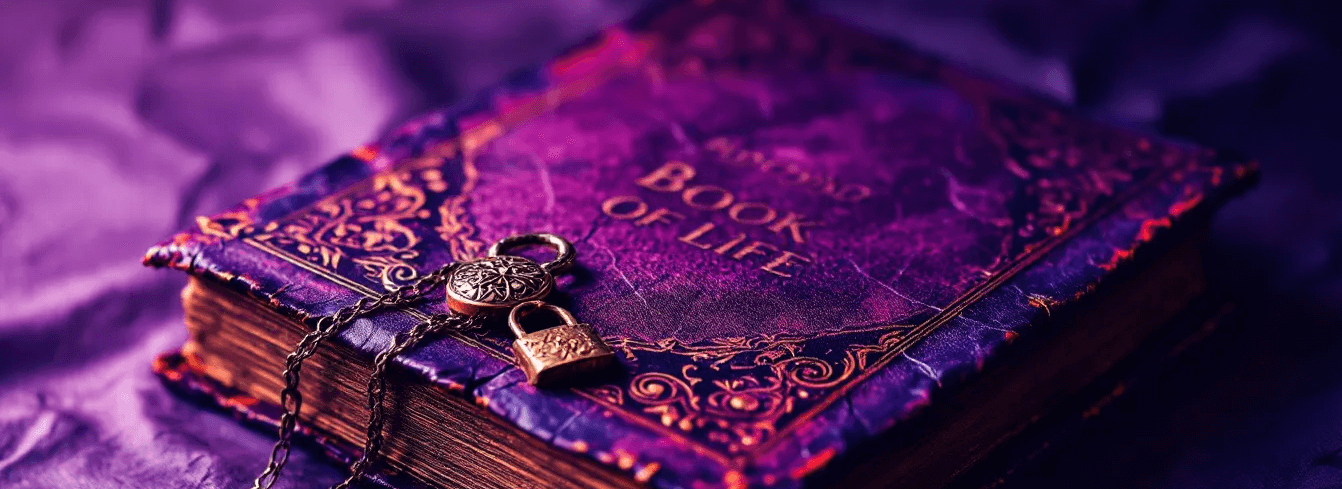
倬云 许
许倬云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成就和对后辈的培养影响深远。
Register of the Holy Name
- 94 years old
- Born on 1930-09-03 in China
- Passed on 2025-08-03 in United States
许倬云是台湾著名的历史学家,出生于福建思明(今厦门),祖籍江苏无锡。他在国立台湾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许倬云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中国古代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等多个方面。
许倬云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任教期间,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历史学者。1980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是对他学术成就的高度认可。1970年,许倬云移民美国,并在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任教,成为该系的荣休讲座教授。
许倬云的学术著作丰富,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等,这些作品不仅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广受好评,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研究不仅注重历史细节,还善于从宏观角度分析历史发展的脉络,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许倬云在学术生涯中,始终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他的学术贡献不仅体现在他的著作中,还体现在他对后辈学者的培养和指导上。许倬云的一生,是学术探索和知识传播的典范。
Path of Grace
- 1930September 3th
出生
许倬云出生于福建思明(今厦门)。
福建思明
- 1953January 1th
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
许倬云在国立台湾大学获得学士学位。
台湾
- 1962January 1th
任教于国立台湾大学
许倬云开始在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任教。
台湾
- 1962January 1th
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许倬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美国芝加哥
- 1970January 1th
移民美国
许倬云移民美国,并在匹兹堡大学任教。
美国
- 1980January 1th
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许倬云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台湾
- 2025August 3th
逝世
许倬云在美国逝世。
美国
Hall of Grace
Register of Return
"The only real treasure is in your head. Memories are better than diamonds."
- BOFM
陈远:许倬云先生千古
中午在学校附近吃饭,回家之后习惯性看一下朋友圈,结果看到的是许倬云先生去世的消息。
有一段时间,许先生在接受十三邀采访的时候被问及有什么遗憾,许先生说:但悲不见九州同。
因为这个回答,许先生遭到很多非议。
坦率说,有一段时间,我对许先生,也很不理解,他晚年的一些作品,我看完之后都觉得,许先生是不是被TZ了?
我问许先生的助手俊文兄,俊文兄说:你觉得可能么?
我觉得不太可能。许先生那一代人,在战争岁月成长,家困国贫,于是产生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爱与怕。他晚年的著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主体展开。
我和许先生认识的相当早,那时我还在新京报,有一次接到任务,让我采访就许先生的新书做专访。我看了许先生的书,很好读,但太新潮,我对许先生的学术经历更感兴趣,毕竟当年读《西周史》,读的那么投入。那时许先生在南京大学主持一个学术项目,我去南京看他,他说:平生所学,未负师友。
后来我对他的专访,用的就是这个题目。
后来他的历史通俗著作《万古江河》出版,我又和他通了两个多小时的越洋电话,做了几个版的专访,后来我在手记中对许先生的评价,在《万古江河》再版时印在了封面的勒口处,没署我名,大概是出版方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请许先生寓目。
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我有本小书,题为《李宗吾新传》,想请许先生作序,许先生说:近代史,英时兄作序更恰当。
我说:寄给余先生,光邮途上的时间就要月余。
许先生说:那我就勉强写一篇吧,你不要着急,我会很认真的写。
结果出版方着急,一直问我:许先生的序什么时候写好?
我打电话给许先生,许先生说:书稿还没有收到。
我又联系快递,结果是卡在学校门口,许先生又派人去南大校门取了快递。但因为时间紧,只能写了篇短序。后来许先生说,他读了书稿,很有感触,同时也认为我在那本小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有些价值,本来是计划写一篇长序的。
因缘际会,我和余先生以及许先生都有一些联系,后来不揣冒昧,写了一篇比较二位前辈的短文,他们二位,应该是都看到了,但都未置可否。大概是我说的不差,但二位前辈都不愿意被比较。
又过了几年,有个朋友的杂志,想作许先生的专访,联系不上许先生,于是想到了我,我又给许先生打电话,做了一篇访谈。
中间还有一次,我想去台大访学,问许先生能否代为说项,许先生说:没问题,这边我来解决,你那边你自己想办法。后来许先生说,他已经和台大说好,我可以着手在这边办手续了。结果我没有办下来,抱歉地告诉许先生结果,许先生说:那就再找机会。
许先生对于晚辈,是这样的有耐心。就像他在《万古江河》里说的:为什么在晚年还要费心费力的写一本通俗性著作?是因为他想通过这样一本书,拉起年轻人对历史的兴趣。
再后来,俊文兄赴美做许先生的学术助手,把我的字给许先生看,许先生说了很多提携的话。
许先生九十生日,我写了一幅祝寿联:
鲐背犹思,思家思国思天下
江河遍阅,阅人阅世阅文章
现在,许先生走了,我很难过,因为我曾经对许先生的误解,他说过对伟大人物,已不再有敬意和幻想,他说过他真正的归宿是历史上永远不停的中国。我怎么可以对这样的人物有所误解呢?
许先生安息。
(本文原载于陈远先生公众号《吾庐道场》,获作者授权转载收录于“昨日银行”平台。谨此致谢陈远先生对“昨日银行”理念的认同与支持。)
Pray
"When you pray, be honest. God knows the truth anyway."
- Tue, Aug 5, 2025 3:17 AM
愿许老一路走好! ——文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