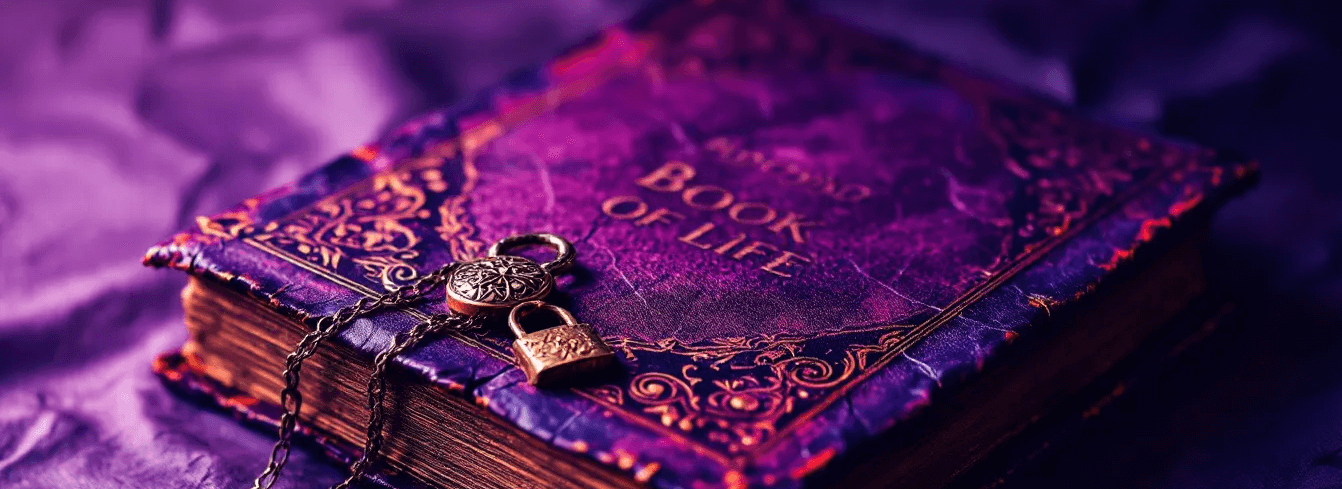
国涌 傅
一位用细节还原历史温度的思想者
Register of the Holy Name
- 58 years old
- Born on 1967-01-01 in China
- Passed on 2025-07-07 in China
傅国涌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者、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以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他出生于浙江温州,毕业于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傅国涌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国史、知识分子史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文化变迁。
傅国涌的著作丰富,包括《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忆》、《民国年间那人这事》、《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等。他的作品以史料详实、视角独特、文笔流畅著称,深受读者喜爱。傅国涌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也是一位积极参与公共讨论的知识分子,经常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就历史、文化和社会问题发表见解。
傅国涌的研究特别注重从个体生命史的角度切入历史,通过挖掘普通人的日记、书信等私人文献,还原历史的细节和温度。这种研究方法使他的著作既有学术深度,又具有很强的人文关怀和可读性。
值得一提的是,傅国涌还是一位热心的历史教育推广者,他经常举办公开讲座,向公众普及历史知识,特别是向年轻人传递正确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不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的重要工具。
Path of Grace
- 1967January 1th
出生
出生于浙江温州
温州
- 1985September 1th
考入杭州大学
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学习
杭州
- 1989July 1th
大学毕业
从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
杭州
- 2011January 1th
出版《百年辛亥》
出版代表作《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忆》
北京
- 2025July 7th
去世
心脏病突发
中国杭州
Hall of Grace
Register of Return
"The only real treasure is in your head. Memories are better than diamonds."
- BOFM
悼念傅國涌
文/高瑜
昨天看到傅國涌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猝然離世的消息,心臟猛然緊縮。一天一夜,他親和、易激動的面龐一直在我眼前晃動。
我和他結識在獨立中文筆會一次境外的會議上,總有小20年了。因為南北地域關係,我們見面機會都是在境外會議上,國內少有見面機會,尤其在我的微信被封,寬帶、手機、座機再被封之後,可以說被阻斷了聯繫。
今天國內多家“公眾號“,都刊登了他的紀念文字。江澤民任上推出“三個代表”,還提出“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文化精英”的概念,但是他這位被各大報章網站紀念的著名學者,到底能不能進入江澤民劃定的“文化精英“的範疇呢?
傅國涌畢業於溫州教育學院,當過鄉村中學語文、歷史課教師,後來就職於企業,世紀之交遭遇政治厄運,只能靠賣文為生。沒想到他發奮圖強,著書立說,十幾年時間,便進入著作等身的的名人行列。維基、百度都稱他為“自由撰稿人”,但是在體制看來這相當於“無業”,如何能進入江氏”文化精英“的範疇?
像傅國涌這樣有文化建樹的人,重新進入體制按說也不困難,92歲的游本昌都可以加入共產黨,何況60後的傅國涌呢。傅國涌與體制的主要隔閡在於他的自由主義思想。他推崇的是民國歷史,他傾注一腔熱血,書寫民國報業、出版業的歷史,大知識分子們的歷史、民族資本家的歷史、中國第一代律師們的歷史,甚至為民國中小學寫傳,以那時的學生為幸 。所有的寫作激情都來源於思想的共振。甚至他的寫作計劃裡,還有為中國思想解放的先鋒林昭寫傳。
當今公共知識分子中流傳著這樣四句話:“活得長;病得晚;老得慢;死得快。“因為他們即使有高俸祿和高津貼,仍舊比不上國家級別的高幹,還是經受不了長臥病床給家庭帶來的消耗。而作為布衣學者的傅國涌,沒有前三句,只落下了第四句。
7月7日凌晨,他突發心梗,兒子傅陽就伴在身旁,但無任何回天之力,他只有58歲半,但願他的靈魂已經順利升入天國。2008年傅國涌已經信仰基督教。
在網上看到他7月6日晚8點06分發的視頻,他只評論兩個字“開窗”,他的一生著述,也是在開窗,推開專制政體的鐵窗,讓自由的空氣進入。
2014年我被傅政華魔爪構陷,傅國涌曾發文聲援,如此俠肝義膽,令我銘記於心,畢生不忘。
本文为昨日银行从X媒体高瑜@gaoyu200812转载,未与原作者联系上,如有版权问题,敬请要求删除。感谢原作者的写作。我们致力于保存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人与文字。
- BOFM
悼念傅国涌先生
文/陈远
7月7日凌晨,在群里看到有朋友发布了傅国涌先生的死讯。
非常惊诧,把消息发布到朋友圈,青岛的李洁兄看到了,比我还要惊诧,立即发消息给我:怎么可能?他昨天还在发朋友圈!
李洁兄劝先把朋友圈内容删掉,等确认的消息。
我心里其实对消息是确认的,谁会拿这样的事情来开玩笑呢。
但我想,这样悲伤的消息,让人晚一点看到也好。
我和傅国涌先生相识,是经由范泓兄长介绍的。老范热心,他的朋友,他几乎都想让我认识。我那时在新京报编副刊,老范跟我说:如果不为难,就多发发国涌的稿子,出了稿费,他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多发点他的稿子,可以改善他的境况。
我当然乐于遵从。写信给傅先生,他马上回信,并附上了几篇稿子。都很长,他在信中说:我的稿子都很长,可能不太符合现代报纸的要求,请陈远兄不要为难就好。
好在当时我在新京报的领导李多钰比较包容,我拿了两个版的版面来发傅先生的稿件,开始的时候李多钰虽然也会皱皱眉头说:太长了吧。但读完文章又会说:文章真是好看。
后来和傅国涌见了面,忘了具体是哪一年,甚至忘了是在南京还是杭州。应该是有老范在场的。我不记日记,也不太喜欢照相。这时想找一点旧日的痕迹,就格外的困难。
如何称呼傅先生,这成了个问题。我和老范兄弟相称,称傅先生为老师,显然不太合适,他比我年长十余岁,直呼其名又显得冒昧,何况傅先生当时有意无意和我们这些媒体从业人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想了想,还是叫傅先生比较好。似乎偶尔也称其为国涌兄。
后来他名气一天比一天大,出书一年比一年多。而我则从媒体抽离。但大家感兴趣的方向大致相同,也总会在一些活动场合见到。联系若有若无。
按理说,我和他应该是有很多共同话题的,细究起来,我们关注领域都在知识分子研究这个范畴之内,都是受到丁东谢泳等诸先生的影响,只不过,他偏重于报业言论史,我则是更关注大学史和学术史。我编过一本《逝去的大学》,向钟叔河先生致敬,傅先生编过《过去的中学》和《过去的小学》,也可以视为向钟先生致敬之作。但回想起来,我们之间的交流却不是很多。
事后想起来,也许当时各自除了自己的研究之外还要为生活奔波而无暇他顾吧。
前一段时间,傅先生从日本归国,老范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回来的消息,我当时也比较诧异,因为时不时能看到傅先生在日本的一些消息,他是很活跃的。老范告诉我,国涌说,实际的情况,也不如外间看到的那么理想。老范还告诉我说:国涌也有些烦恼。
但万万没有想到,他就这样走了。
李洁兄在确认傅先生的死讯后给我发消息说:这样的世界实际上也他妈没有留恋的,除了亲朋好友会悲痛,其实这样猝死也挺让人羡慕,起码不遭罪。
去年苏南兄在老范和海南兄的陪伴下离开,我也曾经这样想过。这是个无常的时代,这是个生者有时会羡慕死者的时代。
前不久,章立凡先生也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白居易诗云: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惟觉少年多。这几年,故人离去的越来越多,让人越发感到这个世界的无常和个体的无奈。更何况,如今的少年们,也是如此艰辛。
傅先生离去的当天,最早是丁东先生在公号“丁东小群”发出的惜别傅国涌,然后纪念文章铺天盖地的涌现,除了傅先生的文章和经历之外,我想,大概很多人都有着他最后发的朋友圈那样的愿望:开窗。
而我,在哀惋之中,把章立凡和傅国涌二位的去世看作时代的隐喻:章立凡先生的去世,昭示了知识分子可以相对自由说话的时代的结束,而傅国涌先生的去世则昭示着知识分子靠写作为生已经没有可能。
早上七点多,章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傅国涌去世了你知道吗?我说知道。章先生说:你写个挽联吧。
我想了想,写下这副挽联:
笔下挟风雷,百年寻梦,寻逝去之传统;
心中期民主,今日遗魂,启后来以山林。
有人留言说,山林本来就是启的对象,我当然知道,但山林也是遗产,也是相传的薪火,更是不死的火焰。
傅国涌先生安息。
本文为昨日银行从公众号吾庐道场转载,未与原作者联系上,如有版权问题,敬请要求删除。感谢原作者的写作。我们致力于保存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人与文字。
- BOFM
惜别傅国涌
文/丁东
今天(注:7月7日)早晨,忽闻傅国涌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噩耗,悲痛万分。他生于1966年11月,还不满59岁啊!
我和傅国涌相识于20世纪末。当时,他刚刚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和他一起承受厄运的陈平,和我是朋友。陈平告诉我,有一个年青朋友,名傅国涌。失去了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准备撰稿谋生。陈平给我看了他的一些手稿,我感到才华思想俱佳。受陈平之托,我在与国涌谋面之前,便将他的文章推荐给相识的报刊编辑。有的编辑比较识货,登了几篇。有的报刊不敢署傅国涌的名字,便署他的儿子傅阳。傅国涌写作速度很快。发表了几篇文章以后,便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觉得刊物对路,就广泛投稿,两三年的功夫,他的文章已经在国内有影响报刊遍地开花。2001年,我应夏中义之邀,参加《大学人文读本》编选工作。这个读本选文三分之一来自世界哲人,三分之一来自中国现代先贤,三分之一来自国内时贤。我将傅国涌的半篇随笔命名为《华盛顿的选择》,向编委会推荐,大家同意收入其中,让国涌也进入时贤行列。读本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后,风行一时。傅国涌很高兴。接着他找来朱锦东投资,约我和谢泳、王丽等朋友选编《中学人文读本》,拿到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在自己的著作《脊梁》一书中对我有所评述。由此成为朋友。
我妹妹丁宁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该社有一套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已经出了二十余种。在策划《胡适传》和《金庸传》时,我妹妹问我有什么合适的作者,我说,那些功成名就的老专家太忙,很难按时交稿,不如请一些正在崛起的学界新锐。于是向她推荐了南京的邵建和杭州的傅国涌。邵建研究胡适很有心得,却不愿意按别人规定的节奏写作,推掉了《胡适传》的约稿。傅国涌承担了《金庸传》。他只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就写成了这部书,而且那五个月的写作时间只有每周的周末,因为星期一到五他还得去一家公司打工。在撰写此书之前,傅国涌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出版史下了很大的功夫,完成了一部专著但没有机会出版。所以,当他进入金庸的报人生涯时,就显示出自己的优势。金庸以武侠小说出名,但他的武侠小说只是办报的副产品,本来是为了扩大报纸的影响而写。金庸首先是一个报人。创办《明报》,付出了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明报》创办于1950年代末,发展于1960年代中。当时正是中国大跃进到文革的那一段。金庸主持《明报》笔政,定位于以“公正与善良”为宗旨的中立立场,由小到大,成为香港舆论界举足轻重的大报。尤其是文革时期的社评,以善于预见事态的发展见长。历史已经证明,在大多数问题上,《明报》的见解是对的,而一味紧跟大陆的报刊,时过境迁,便站不住脚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旁观者清的金庸成了大陆的座上客。金庸虽然早已告别报界,但他当年的报人生涯,仍然不失现实意义。傅国涌这方面的发掘,可谓独具只眼。
《金庸传》在市场上畅销之后,我又将傅国涌的书稿《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推荐给出版家刘硕良,出版后又在市场上畅销,出版社和书商纷纷找上门,从2004年到2006年,他多年积攒的书稿纷纷付梓。接着,他又不断拓荒,从现代报业、出版业的历史,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从现代民族企业家的历史,到现代律师的历史,从现代中学的历史,到现代小学的历史,他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筚路蓝缕,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新天地。二十几年的时间,他在国内和海外,先后出版著作数十种,真正实现了著作等身。
有一段时间,地北天南,不少机构请他演讲,他一度甚至成为电视台追捧的对象。在纸质媒体兴旺的年代,他还成为时事评论高手。一些风格新锐的日报和新闻周刊,遇到突发新闻事件,争相约稿,希望以他的时评为媒体增色。他面对国内发生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热烈地是其所是,鲜明地非其所非,他从百年中国言论史的研究者,又变成以言报国的实践者。他以一介布衣之身,完全凭自己的正气、热情和才华,在公共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后来,报纸杂志媒体式微,出版空间日益逼仄。傅国涌再次转型,潜心于教育,特别是儿童作文。他招收了一些十岁上下的孩子,传道授业解惑,还开门办学,带着孩子们,远赴俄罗斯的皇村讲普希金,波良那的庄园讲托尔斯泰,到英国的哈什福德讲莎士比亚,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讲文艺复兴,甚至把国语书塾开到东京,桃李遍天下。
七年前,我在公众号上发文写他。他当时留下感言:“感谢丁东先生,与他的相遇也是我生命极为重要的相遇,转眼近二十年了。假如没有遇见他,一定不会有我的《金庸传》,我的小文《华盛顿的选择》也不会在十八年前入选《大学人文读本》,并选入山东人民版的高中《语文》课本。是他将我带到李鋭先生家,请李老给我写序;将我引荐给何方等许多老先生……他带我认识老出版人刘硕良先生,推动了《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的问世。十六年前,他应我之约主编了《中学人文读本》。从1999年到2004年,在我早期的研究写作生涯中,处处有他无私的帮助。我虽非千里马,他是毋庸置疑的伯乐。感谢生命中有他,我遇见他时,他在生命的盛年,还不到我此时的年龄。”
回想和傅国涌的交往,从北京,到太原,从杭州,到莫干山,一幕幕相聚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他还约我们去他的家乡雁荡山,因为疫情没有成行。我和小群早已跨过了古稀之年的门槛,还在盛年的国涌却突然撒手而去,怎能不让我们扼腕叹息!
(国涌辞世日上午9时,匆匆而就)
本文为昨日银行从网络收集,未与原作者联系上,如有版权问题,敬请要求删除。感谢原作者的写作。我们致力于保存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人与文字。
- BOFM
隐者傅国涌开窗归去
文/温克坚
2025年7月7日早上7点半左右,看到有朋友在某个群里求证傅国涌病逝的消息,大为震惊!我立刻打开傅国涌的朋友圈,看到他前一天晚上还在转发那个破窗自救的视频(只加了简短有力的两字按语:开窗),我心想,或许只是误传!
但很快就看到更多朋友转发的讣告:傅国涌先生今日凌晨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世事无常,这些年来很多朋友遽然离世,包括天津的MrLee,金华的沈阳,杭州的阮景弘,无锡华春晖,江西葛小智等等,都给我带来极大的心理震荡,而那一年老XIA病逝更是让我长期心理阴郁……没想到,这些年来疏于联系的老友傅国涌,也会以这种让人猝不及防的方式忽然离开!
疫政三年朋友间甚少走动,疫情之后,那种“冷漠”状态似乎变成了一种心理惯性,所以我已经超过5年没有和傅国涌见面。当然,走动不多还有一个原因,我知道疫情后他移居日本,在杭州逗留时间不多。此外,看他朋友圈,除了这些年他专心投入的语文教育,偶尔他也会晒西湖边带孙子的照片,这种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对傅国涌来说,太不容易,我觉得“不去打扰”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我查看和他的微信互动记录,两年多前他发给我的最后几句话是:“真快,我们这一代的时间消磨得差不多了”。“大家都已尽力而为,虽有遗憾,但也坦然。”现在去体悟这些话,其中似乎也隐含着某种直面死亡的乐观心态,我知道,傅国涌多年前已经皈依主,愿上帝怜悯,愿他在天堂喜乐。
不过情绪和记忆涌动,我觉得还是得写一点悼念傅国涌的文字。
2002年前后,我厌倦了原来的生活轨道,借助于互联网所打开的公共空间,和一些原本不可能有任何交集的朋友有了频繁的互动,而很多北京来杭州游玩的朋友,都会提到杭州有个傅国涌,于是我们设法相约一起聚聚,一来二去,我们就熟悉起来,不定期会聚在一起畅谈一番,傅国涌博闻强记,口才滔滔,听他讲述,颇有画面感,很多朋友都甚为佩服。他夫人曹老师偶尔也会参与小聚,傅国涌和曹老师相识于那个特殊历史时刻,他们走过的那段时光想必非常艰辛……曹老师毕业于北师大,但因为傅国涌的牵连,无法找到一个正经中学的教职,只能在一个聋哑学校谋份工作。在那些动荡飘零的岁月,是她给傅国涌带来一些安定感。
回首往事,有几段记忆特别鲜明。北京江老师夫妇是傅国涌故旧,2003年他们来杭州歇个脚,有一天,我和傅国涌陪他们在西湖边散步,路过一公园,我们就在边上驻足旁听。那个年代,一公园被誉为杭州的“海德公园”,每天都有数十甚至数百人在那里聚集,慷慨激昂纵论天下事。记得那天有位老先生说了一句:“5000年来我们都没享受过人的尊严”!饱经命运风霜的江老师和傅国涌也不禁动容。
还有一次,因为耶稣堂弄的旧居拆迁补偿问题,傅国涌和地方政府对簿公堂,开庭那天我和老费等几个朋友前往围观,庭审完毕之后,我们都觉得当时请的律师言不及义水准欠佳,我说这种案子应该请宁波袁裕来辩护,说话间,袁裕来从走廊另一端走过来,原来他刚结束另一个庭审,我们皆感叹缘分神奇,后来我们一起吃午饭畅聊。
正如丁东/邢小群老师的悼念文章里提到的,20世纪末的傅国涌已经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承受了厄运,在人生际遇上,实际上我们有明显的代差。2003年前后,我内心充斥的是对公共事务的莫名兴奋,而傅国涌却已历经沧海,或许基于对历史更深厚的洞察,他对集体激情有着隔阂,有一份冷淡,甚至有一分警惕。在很多事件中,我可以明显感受到他有意选择保持距离。
比如当时的ChinesePen,那个年代很多独立写作者纷纷加入,我也是早期活跃成员之一,而傅国涌则是最早的一批成员之一,但无论我怎样劝说,他都不再参与其中活动,而只是选择作为一个沉默会员。吊诡的是,若干年之后,我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沉默会员,不再参与其中的任何事务。
那些年,我们很习惯参与到集体表达,无论是李慎之先生的仙逝,还是孙志刚事件,不锈钢老鼠事件、李思怡饿死等事件,都有一波波的集体表达,傅国涌关注这些事件,但他往往选择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而婉拒集体参与。
傅国涌的这种选择,既基于他理念层面的保留,更主要的是他必须面对现实的生活压力。从那些热点公共事件中退后一步,傅国涌有了时间和空间,通过写作换取一些收入,他曾经告诉过我,每天他都要至少写几千字,否则心理不安。从丁东/邢小群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朋友给予了他帮助,他也影响了大量的朋友。
傅国涌第一本有影响力的大作是《金庸传》,这本书因为披露了一些新的信息,引发了金庸的不满,公开指责作者从来没有采访过他。傅国涌认为,金庸的指责毫无道理,首先并非他不愿意采访金庸,而是多次联系未果,其次很多传记作者都不可能采访传主,比如那些历史人物传记。不过据说后来金庸认真看了这本传记,发现对他的评价相当高,因此也就释怀,后来还托人带话给傅国涌表达善意。其实傅国涌自己对这本传记并不满意,觉得假以时日,可以写得更好。不过因为这本书,他卖字为生的通道打开了,此后他笔耕不辍,陆续出版了多本著作,包括《历史深处的误会》《追寻失去的传统》等等。他写林昭,写卢作孚,写49年前那些律师,他的笔端饱含激情,他的历史叙事中价值张力拉满,细心的读者能感受到和现实相关的咏叹调。
傅国涌多年勤奋写作有了回报,那些著作给他带来了公共声誉,在那“公知”依然是一种赞许性称谓的年代,傅国涌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员,他也可以在很多公开场合发言,他那滔滔不绝的表达能力给他带来了更多拥趸。
但在我眼里,傅国涌后来获得的这些声誉都是辅助性的,他早年的那些选择和担当才是独一无二的。时代浪潮之下,社会多重嬗变,而公共领域则是支离破碎,后来的傅国涌更像是一个隐者,隐身于历史和文化研究,这些当然是他热爱的领域,但其中有多少无奈,或许也不足与人道。前些年傅国涌亲力亲为,给学童办起了文化课堂,在小圈子内声誉鹊起,不少朋友都把小孩托付给他,对我来说,作为教育者的傅国涌已然有点陌生。如今他逝去,我再也没有机会和他交流这些年来他的心路历程了。
不过这些并不重要,有些闪亮的时刻可以对抗时间的侵蚀,犹记得2010年10月中旬,我、老莫和傅国涌一起吃饭,那天他慷慨激昂,言辞滔滔,眼里有光。
2025年7月8日
本文为昨日银行获得温克坚先生授权转载,原文首发于公众号新新默存。感谢原作者的许可与信任。我们致力于保存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人与文字。
Pray
"When you pray, be honest. God knows the truth anyway."
Leave the first pray!